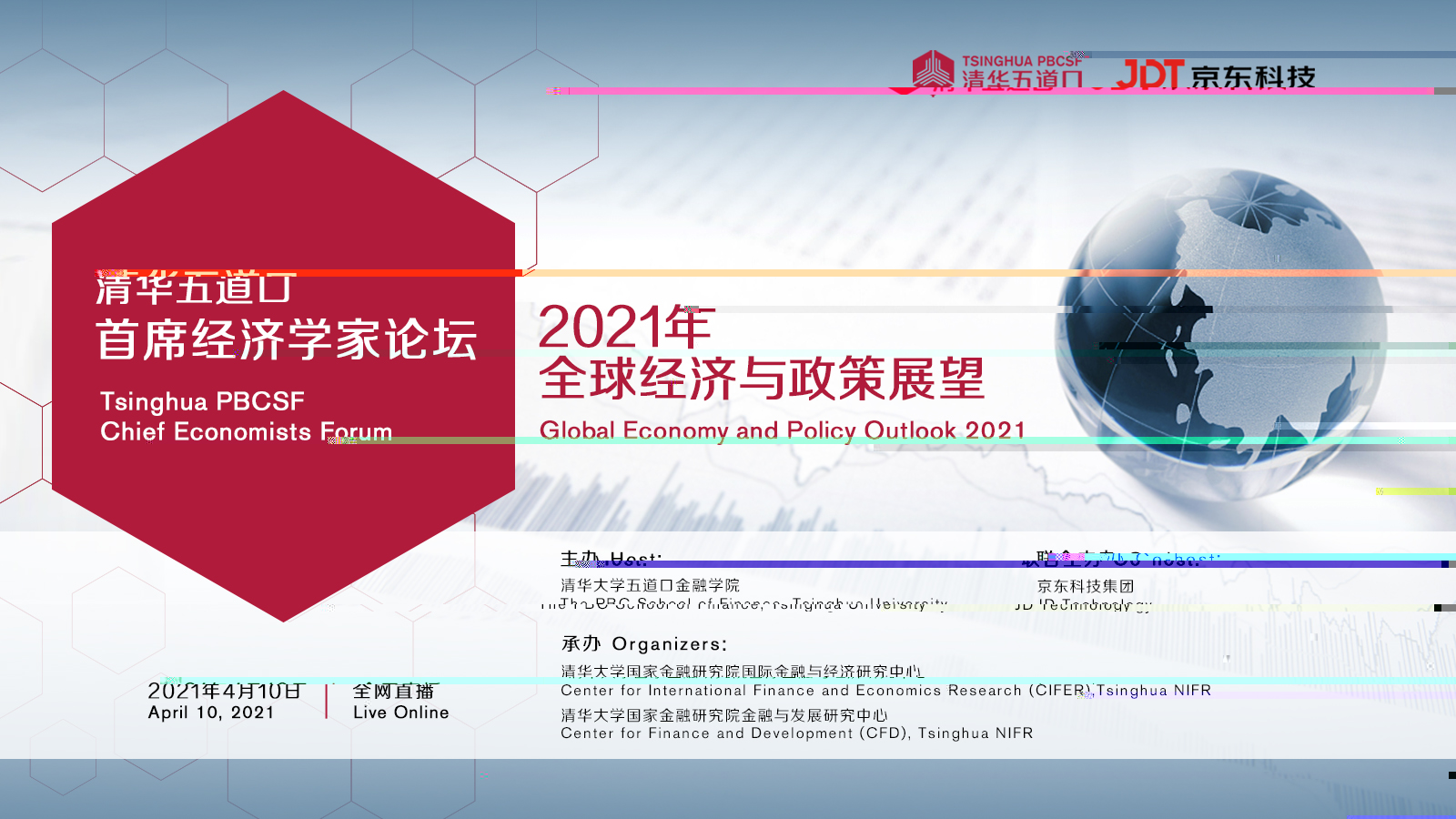
2021年4月10日,闊别兩年的“Betvictor中文版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雲端回歸。
由Betvictor中文版(PBCSF)主辦、京東科技集團聯合主辦、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CFD) 承辦的 “Betvictor中文版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2021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在27個平台全網直播,受到近百家媒體矚目,直播觀看人數超千萬。
本屆論壇以主旨演講+圓桌讨論兩部分組成,采取線上參會、全網直播的形式,讓觀點交流、思維碰撞暢通無阻。論壇邀請到二十餘位重量級嘉賓相聚雲端,圍繞全球經濟展望、中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展望、後疫情時代的貨币和信用、碳中和與宏觀經濟等話題展開深入讨論。論壇由Betvictor中文版紫光講席教授、國際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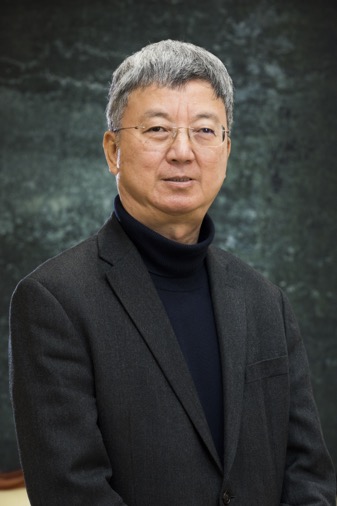
朱民院長
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出席論壇并發表主旨演講,他表示,2021年宏觀經濟政策應推動增長和平衡并重,并多次強調結構與質量高于總量。朱院長認同肖主席提到的經濟分化的問題,2020年各國政府專注于應對疫情沖擊下的經濟衰退,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動經濟總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後果造成了結構性的經濟活動不平衡,也對我國過去十年國内經濟增長的大格局産生結構作用。相對總量,2021年的政策應當偏重結構性恢複,三個比較大的抓力表現為:一,老齡化的速度遠遠超過想象,會改變需求、改變供給和改變金融。二,2060碳中和不但是能源革命,還是技術革命。中國面臨的轉型的挑戰比歐洲要大。三,數字化轉型,數字變成資源和資産,會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禀賦,重新定義國家的核心競争力。在這三個背景下,宏觀政策面臨三重任務:修補過去的不平衡、推動經濟的強勁增長、面向未來的結構優化經濟增長範式的轉軌。這是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最大挑戰。現階段保持寬裕的流動性還是很重要,但2021年财政政策的精準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朱民院長發言中
以下為發言全文(未經嘉賓審閱):
朱民:首先感謝建東組織和主持這個活動,我也借此機會以國家金融研究院的名義對參會所有嘉賓以及所有在線的聽衆和觀衆表示歡迎和表示衷心的感謝!在周末的上午來參加學術讨論,這還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非常感謝,特别是感謝各位嘉賓、各路英雄都來齊聚五道口讨論天下的大事,還是很好的一件事,表示感謝!
今天是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參會的都是各路大家,對經濟的觀察是非常細微的,而且每天跟蹤。所以,我在這方面就落後很多了,對我來說是一個向大家學習的機會,不算冒昧,接着肖主席的後面簡單把我對宏觀一些觀察給各位嘉賓、各位聽衆和觀衆做一個簡要的彙報。
我也想沿着肖主席剛才說的思路,就是分化的問題,我想讨論的問題就是2021宏觀經濟政策,推動增長和平衡并重。
對于近年來說,全球包括中國整個宏觀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總量,也要看到結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變量。2021年經濟大家都看到了,疫情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衰退,在2020年的時候,其實各國政府主要關注走出疫情、推動經濟反彈,所以,總量是當時的主要的政策目标,我們也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财政政策、貨币政策等等,要把總量控制住,能夠讓它反彈。
2020年年末的時候,我們看到全球經濟-3.3%的衰退,這個看的很清楚。與此同時,更多的在衰退後面是一個經濟結構、經濟活動出現的一個新的不平衡,這個很有意思,和以前的很多危機不一樣,因為疫情的沖擊對不同的産業、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地區産生不同影響,剛才肖主席提到國家政策不一樣,産生了對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影響,這個現在看來很清楚,我們可以看到,從國家地區來說這個差距很大,最典型的差距還是表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幾乎要變成永久性鴻溝,這個鴻溝在拉大,這既是意外,也是很令人不安的現象。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預測對未來兩年的展望,2020-2022年這幾年,整體的預期損失,新興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能人均損失20%,發達國家隻跌11%。這個差距還是很大的。整個經濟恢複,拉美地區、中東地區、非洲地區整個複蘇相對都是弱的,這個很有意思,和發達國家比之所以弱,有很重要的原因,當然是财政刺激政策的力度比較小,發達國家總體用12%以上的财政,新興經濟國家用8.6%左右,發展中國家隻有5.6%左右的财政刺激,沒有财政空間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國際通用的儲備貨币的貨币地位,所以,就不可能擴大财政。儲備貨币地位成為了劃分經濟刺激政策空間和經濟發展反彈速度和結構,變成一個特别特别新的現象,這還是很特殊的現象,這個現象可能也會影響今後持續不斷的發展。
但是,不平衡反映在方方面面,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個看的很清楚。實體經濟衰退3.3%,美國資本市場反彈非常強勁,虛拟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不同步,這個也看的很清楚,由此反映到就業的人群,低收入、低技術的年輕人、婦女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遠遠大于一般的平均的勞動力受到的影響,就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幾乎又有近1億人重新回到赤貧境地。現在看來,結構的變化需要引起關注,這是國與國之間結構變化,這個也是國内産業之間以及不同的就業人群等等一系列變化,這個也是特别需要引起關注的。
從大的格局看,中國2020年2.3%的強勁反彈,這是世界上唯一大國的正增長,這是了不起的成績。在2.3%下面,我們也看到整個經濟活動不平衡,隻是說經濟活動還沒有到形成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一點,如果我們能及時采取措施彌補和止住的話,但是,經濟活動的不平衡進一步擴大,已經變的很清楚。從總供給側來看,工業反彈很強,服務業反彈很弱,因為服務業跟人的接觸密集型,比如旅遊業是6.6萬億元人民币的大産業,跌了近60%,餐飲業也是近6萬億的大的行業,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對和人密切接觸的服務業影響很大。
從總需求側來看,去年我們國家投資還是貢獻很大,投資占整個GDP的52%以上,進出口貢獻占13%,消費很低,從增長的角度來說,消費還是負貢獻。
我們過去10年來發展的基本的趨勢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因為中國在走向服務經濟,服務應該的比重其實一直在逐年上升,制造業、工業從2012年、2013年頂峰以後一直逐漸下降,而且消費為主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内市場為主的大的格局正在逐漸形成,2019年、2018年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都高達60%、70%左右,正在走向國内市場,雙循環有一個很重要的立腳點就是國内市場,疫情卻對根本的結構和經濟活動趨勢産生了逆向沖擊,這就需要考慮我們的方向還是應該怎麼走。
從工業内部來看的話,制造業反彈還是強勁的,但是,制造業反彈推動上遊反彈更強勁。所以,工業内部也産生新的分化,因為疫情的影響,在制造業内部,大型企業的反彈遠遠強于中小企業的反彈,也是由于疫情的根本性質決定的。剛才肖主席也講到,從區域來說,從東西的差别擴大到東西加上南北的差别,這是疫情産生的一個新的現象,包括增長的差别,包括人均GDP差别,包括收入差别。我們在縮小收入差别,走共同富裕之路時候,這個沖擊又是一個很大的沖擊。
勞動力市場看的很清楚,年輕人、低技術人員、短期的工人、農民工受到的影響很大,特别是農民工,在2020年入城數量急劇下跌的,形成了整個收入差别的擴大。所以,這個都是經濟活動發生新的結構性不平衡的現象。這個不平衡現象和我們過去十年來政策的導向其實是有逆向作用的,這就是疫情的沖擊。
站在2021年的時候,當我們強力推進經濟反彈和恢複的時候,看到總量,更多的看到結構,特别是政策偏重結構的恢複,再平衡就變的特别重要。
第三點我想說的,當我們說疫情對經濟造成結構性的經濟活動的不平衡的時候,在2021年起點上,還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結構的轉換,結構的轉換,時間關系,我可以舉三個比較大的抓力:第一,老齡化,老齡化的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們今天已經有12%65歲以上人口,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到2035年和2050年速度和規模都會非常長的非常快。用2050年人口結構和今天人口結構比的話,2050年整個淨增人口都在60歲以上,60歲年齡段的人口會增長8000萬,70歲年齡段淨增1億,80歲年齡段淨增8000萬,60歲以下年齡段人都是淨減,特别是40歲年齡段淨減8000萬,20歲年齡段淨減1億,老齡化和長壽化這個結構變化是巨大的,這個結構變化從根本上改變需求、改變供給,也改變金融,因為未來養老保險變成很大的事情,舉個例子來說,從日本經驗來看,日本是老齡化最早的國家,從1994年到今天的數據來看,制造業、建築業包括金融業占經濟比重都是萎縮的,隻有醫療、科技、通訊這些行業是發展的。當然,老齡化引起潛在經濟增長素質的下跌和低通脹膨脹率。
第二個大的結構性變化就是2060碳中和,這是總書記在聯合國鄭重承諾的,最近大家非常熱烈的讨論碳中和這個事情,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是環保,是排放,這是必然的,但其實源源不止這些,煤消耗占60%以上,把煤降到6%左右,後面是技術革命。從根本上走向綠色發展的道路,是根本的發展方式和發展範式的改變,中國會由此告别傳統的西方300多年工業革命以來的以石化燃料為基礎的工業發展軌道,開始走綠色為主的發展軌道,這是前人沒有的。比如說歐洲走中和的時候,還是有幾個相對比較有利的條件,第一,人均GDP水平很高,第二,服務業占比很高,70%以上,碳排放很低,第三,增長速度很低,2%左右,低增長、高服務業的情況下,碳排放達到峰值以後往下走,而且時間比較長,從1990年到2050年,60年時間,空間比較大。
我們要面臨同時要增長,人均GDP隻有1萬美金,增長就要消耗能源,同時,還要減少排放,走綠色的道路,而且時間從現在開始到2060年隻有40年,時間比較緊,轉換規模很大,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很多技術路徑是不影響的,比如說車,我們規定2030年40%電動車,車的另一個科技路徑是氫,氫能源可能會發生很大作用,包括煉鋼,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變化、産業變化,會根本引起重塑整個制造業,而且對整個經濟包括人的活動都産生變化,這是新的發展範式,這又是一個新的均衡。
第三,數字化轉型。疫情意外的發生,就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并且轉到科技摩擦、科技競争,科技競争變成全球競争。當然,别無選擇,需要走自己内生的科技創新發展道路。同時,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這樣的思路,通過把經濟數字化來提升我們的核心競争力,經濟走到1萬美元以後面臨中等收入陷井這樣的挑戰用科技的辦法有效的予以化解。
數字化進展非常快,我看很多企業,特别是制造業,不用說商業、不用說物流,重型企業數字化生産,三一重工,重型設備上APP,家電的制造業,美的的空調現在流水線智能化、數字化發展非常快,美的一台空調勞動力成本隻有人民币的10塊錢,以前真是很難想象的,整個數字化過程會根本改變一個國家的核心競争力,數據變成了資源,科技能力、算法變成了勞動生産率,這個國家的競争地位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是數據大國,因為人口多,14億人口,因為互聯網上網的人多,7.8億,全球第一。而且我們流量用的多,我們分析中國人現在人均月流量是9GB,高于OECD國家的50%,他是6GB,10年以後,2030年人均流量大概會達到100GB/月,很多人指出我這個預測可能還是保守的。上網人多,流量多,國家在大力推進物聯網,我們去年物聯水平達到10億級,和OECD國家總量相平,10年以後會達到100億級。人和物同時在産生物主的數據,數據變成了資源,而且正在變成資産。
兩個禮拜之前,北京成立了北京國際數據交流中心,成立了北京數據交易聯盟,開始把數據走向資源、把數據走向資産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這個都是未來巨大的結構變化,因為在根本上重新定義核心競争力,重新定義一個國家的資源禀賦,重新定義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把這三件事放一起看的話,今天在這個節點上,我覺得宏觀政策确實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個宏觀政策,要繼續走出疫情的危機,推動經濟增長,那是毫無疑義的,比較高的和領先的是2020年已經初步走出了疫情,今年的定位其實不是走出疫情,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發展,這個很重要,因為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包括美國今天還在走出疫情這個階段,通過疫情發展第一階段是危機,迅速的把危機下跌止住,财政、貨币政策,2020年都看到了,然後走出危機,這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定位,然後才是在新基礎上考慮可持續未來的發展。中國整整領先全球經濟複蘇一個周期,大部分國家都在考慮走出危機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出了,我們在考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階段,總量不重要,結構重要。總量不重要,質量重要。因為這是打新基礎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疫情對結構客觀上已經制造了一個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補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的不平衡,我們可以看到産業之間的不平衡,虛拟經濟金融和實體的不平衡、虛拟和實體的不平衡、區域的不平衡、就業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剛才肖主席也提了很多,我們要修補這些,回到我們自己的結構和發展的基礎框架上,這個很重要,不能由此形成一個持久性的傷痕,我們分析曆史上過去近百年來各種危機,政策上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過度的看總量、忽視結構,以至于疫情或者危機變成結構變化的轉折點,制造了一個持久性的傷痕,而在以後會花相當長的時間來改進。
2021年政策偏重結構,修正疫情造成的結構的不平衡,我覺得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與此同時,還要面向未來,就是看到我們的老齡化、看到碳中和起步巨大的發展範式的改變,看到數字化轉型,推動整個經濟朝這三個方向走,從而能把中國經濟放到一個永久性的、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軌道上,這個任務就變的特别特别的重要,這等于是三重的任務,要修補過去的創傷,要推動經濟的強勁增長,同時,還要面向未來的結構優化轉化,整個經濟增長範式的轉軌,這是今年宏觀政策最大的挑戰。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年人大上國家把今年經濟增長目标定到6%,我覺得6%以上就很好,這就不是過分的強調總量和數量,而是看到了結構和質量的重要性,已經邁出了特别重要的步伐。剩下的就是政策發力要求會更加的困難,央行貨币政策,全球都在繼續刺激寬松和開始收緊的轉換和猶豫的階段,我們現在看的很清楚,市場也在不斷的變動,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大的波動,在現在的情況下,保持寬裕的流動性還是很重要,中國利率水平現在已經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經快于國際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所以,貨币政策還是要保持寬松,支持流動性還是很重要。
但是,在這個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精準發力變的特别重要,因為财政曆來是調結構最有力和最關鍵的工具,結構調整其實是兩個方面,一個對疫情危機造成新的不平衡的修補、恢複,這是一大塊。面向未來的結構調整,引領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更大的一塊。所以,财政在2021這個節點上政策的精準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從國際上來看,對新一輪财政讨論還是很熱的,究竟怎麼樣合适,能夠維持一個平衡。
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在這次疫情中采取了理性的、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的規模,跟國際水平比,都是中等、中等偏下,既看到了我們已有的風險,高債務;也看到了傳導機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細微滴灌的辦法逐漸的推進,提高它的效率,給我們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留酉空間,在今天這個節點上用好這個空間,精準定位,兩個方向都要布局,抓好結構轉型,我覺得是大事,總量不是今年的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結構恢複、發展、轉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1年在中國曆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為是“十四五”的起點年,是中期計劃的起點年,由此,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年,所以,今年以及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新的發展範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就變的特别的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更多的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标。
我的發言就簡單講到這裡,把我的觀察給大家做一個彙報。在座的各位是真的大專家,所以,我待會兒靜靜的聆聽各位的高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