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普通人,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我還能自信嗎?”
相信這樣的疑問存在于不少人的頭腦之中。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到底應不應該自信呢?
普通卻自信,你怎麼看?
第一種:我雖然普通,但是自信與普通并不沖突
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會認為自己是一個普通人,畢竟驚天動地的成就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取得的。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發出光和熱,盡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哪怕是并不太起眼的普通人,也一樣可以自信。畢竟自信是力量之源,能夠對自己有着更好的激勵作用。
第二種:我應該認清自己的普通,總不能明明很普通,還不停地“自命不凡”
也有一部分人認為,人貴在有自知之明,能夠對自己有清醒的認知,以及對自身能夠有合理的定位,而不是盲目的“自信”,錯誤地認為自己擁有着高人一等的能力。
兩種觀點各有立場,那如果我很普通,到底還應不應該“自信”呢?

l 什麼是“自信”?
自信(self-confidence):自信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心理系統,是個體對自己的積極肯定和确認程度,是對自身能力、價值等作出正向認知與評價的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特征(車麗萍,2011)。
自信定義中的“相對性”是指,自信既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又受具體情境的影響,可以說有多少種情境就有多少種自信(車麗萍,黃希庭,2006)。
此處我們談到的“自信”更多的是指适度的、合理的自信,在對自己有清醒認知基礎上的自信。
l 什麼是“普信”?
“普信”更多的是指“過度自信”,或者是超過自身實際能力範圍的自信,或者也可以稱之為“自戀”。
自戀常被認為是個體高度自信、尋求關注的表現 (Morf & Rhodewalt, 2001) 。但在現實中,自戀的概念要複雜得多,現代心理學認為,自戀是一種認知、情感和行為的綜合體,是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特征(Campbell, Bush, Brunell, & Shelton, 2005)。其特點是具有個人優越感(Campbell, Goodie, & Foster, 2004; John & Robins, 1994),誇張(Morf & Rhodewalt, 2001),支配欲和對權力的渴望(Emmons, 1987),對他人注意力的渴望和對其優越性的确認(Bogart, Benotsch, & Pavolic, 2004),以及缺乏同理心 (Brunell et al., 2008; Lubit, 2002; Rauthmann, 2012)。
自戀者關注于權力、自我形象等個體特質 (agentic trait) 而非同理心、助人等集體性特質 (communal trait) (梁燕,崔麗瑩,2019)。

擁有健康水平的自信和自尊(這對大部分人來說是有吸引力和有用的品質)與自戀之間的區别在于自戀者有更高的自我價值感,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比别人好。也正因如此,自戀者往往會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并由于其同理心的缺失而貶低他人。
自戀的成因衆說紛纭,其中“面具模型”被部分心理學家所接受。誇張和自信等自戀特征通常被稱為“面具模型”,據說是為了掩蓋内心深處的自卑感。為了解決這種差異,自戀者通過尋求他人的積極反饋和自我肯定來進行自我調節(Bosson et al. 2008, Morf & Rhodewalt 2001),而調節的結果就是“矯枉過正”,用過分誇大的信心來彌補和欺騙自己,以回避自卑帶來的負面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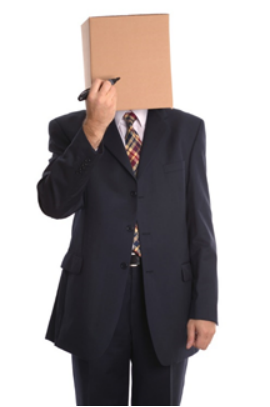
人們為什麼讨厭自戀者?
首先,在人際關系方面。自戀者在最初往往表現出較強的魅力,然而這種魅力也是一把雙刃劍。盡管最初被其他人喜歡,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人會變得越來越令人讨厭(Paulhus, 1998)。在浪漫方面,這些人更傾向于不忠和遊戲式的親密關系(e.g., Campbell et al. 2002; Miller et al. 2013)。在新婚夫婦的婚姻前四年中,自戀能夠明顯預測夫妻雙方的婚姻滿意度下降(Lavner et al. 2016)。這些人給自己的“重要他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Miller et al. 2007)。病理性的自戀總是以嚴重的人際關系障礙為代價的。
在工作場合中,自信往往被認為是具有領導價值的表現。有信心的領導者樂于迎接挑戰并設定困難的目标(Luthans et al .2001)。領導者的自信同樣也增加了追随者朝着領導者目标努力的意願(Luthans & Peterson, 2002)。但問題是,這種領導特征并非總是有益的。自戀可能是領導者做出糟糕決定、繼續實施失敗計劃、忽視明顯缺陷的根本原因。這些行動帶來的後果不僅是不便,而且相當有害,就像曆史上布什決定攻打伊拉克和拿破侖進軍莫斯科的事件一樣。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些人似乎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自戀者的影響。
Butzer和Kuiper發現,自我不确定性高的人比自我不确定性低的人更容易進行社會比較。Weary、Marsh和McCormick(1994)還發現,對自己的觀點不太确定的人更有可能被激勵将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
Morse和Gergen(1970)發現,當一個人與社會上受歡迎的人在一起時,他的自尊水平會下降,而與不受歡迎的人在一起時,情況正好相反。關于社會比較頻率與自尊之間的關系,Campbell(1990)發現,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更容易進行社會比較,低自尊的人對社會比較信息更敏感。Gibbons和Buunk(1999)還發現一個人的自尊和她的社會比較頻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研究者發現,Meta(原Facebook)上的社交比較頻率與通過比較産生負面感覺的頻率(即,認為他人的生活和表現都比比較者好)之間存在正相關。這種正相關性可能是由幾個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個人的心理特征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例如,與高自尊和低自我不确定性的人相比,低自尊和高自我不确定性的人可以進行更多的比較,并從比較中産生更多的負面情緒。其次,用戶可能會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更多關于自己的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而“幸存者偏差”效應則會讓網上沖浪的人們堅信“别人的生活都很美好”,進而得出“隻有我是失敗者”的結論,進而引發消極情緒。

總而言之,自戀者由于其誇張、低同理心等特點,往往很難經營好一段親密關系,在工作當中也會造成潛在的風險。與此同時,人人都會和身邊的人比較。而自尊水平較低、習慣懷疑自己的人更易受到其他人的影響。當這種類型的人遇到了自戀型的人炫耀自己,他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缺陷和對方所炫耀出的優點進行比較,比較的結果往往是“我很差,我是loser”。與此同時,部分人也會在此基礎上加深對對方“自戀”的反感,就像陰影在烈日下會顯得更加陰暗一樣。而在網絡盛行的當今社會,所有的優點甚至都進一步加上了“濾鏡”和“選擇器”,讓這種對比效應進一步放大,加深人們的焦慮感。
作為普通人,我到底該不該自信?
答案毋庸置疑——當然應該。
自戀之所以會被人讨厭,其核心往往在于“支配”、“過分誇張”和“低同理心”。大部分自戀者僅僅是有自戀傾向,不會達到病理的程度。所以隻要你的自信不是無理地要求别人、忽略别人的感受,完全以自我為中心,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對每個普通人來說(再優秀的人,在别人眼裡可能也是普通人),擁有健康的自信也是一種非常寶貴且健康的品質。

在電影《當幸福來敲門》中,有着這樣一段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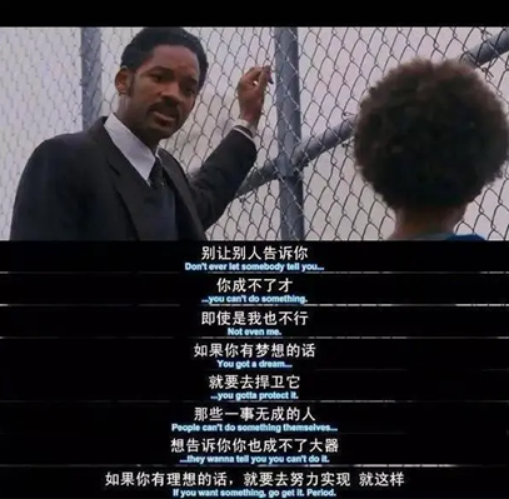
圖源:《當幸福來敲門》
父親和兒子曾經過着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兩個人的狀态已經不能說是“普通”,甚至帶着一些“悲慘”。然而此時父親仍然鼓勵自己的孩子要滿懷信心的生活下去,哪怕被别人貶低也不能放棄自信。
同時也需要注意到,自信這件事也被文化環境所深深影響着。在拉丁美洲,那裡的人們都對自己的身體無比自信。他們認為與其掩蓋“缺點”,還不如放大優點。曾經有一個在拉丁美洲某城市的街頭采訪,主持人随機問路人:“你覺得自己好看嗎?你最喜歡自己外貌的哪一部分?”。被采訪男女老少都有,大部分人的顔值也都處于普通水平。然而大家的回答卻出乎預料。這其中,80% 的人都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覺得自己很漂亮/很帥”,并且都能幹脆大方地說出喜歡自己的哪一部分。而另外 20% 的人回答 :“我覺得自己不能用漂亮形容,簡直是沉魚落雁 /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而那些覺得自己很好看的拉美人,真的都是“完美”的嗎?當然不是,有的甚至相差甚遠。他們自信的回答,也許含了幾分玩笑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一種他們選擇的人生态度。在拉丁美洲的男男女女,都會樂于展示自己“與衆不同”的部分,O型腿、雀斑、小肚子,這些被我們認為“醜陋”的身體特征卻被他們作為“獨特”而自信地展示出來。的确,到底是誰定義了美和自信呢?
中國人自古就有“謙虛”的美德。“謙受益,滿招損。”、“虛心萬事能成;自滿十事九空。”然而也正是這種崇尚謙遜的文化環境,讓很多國人不敢自信,不知道該如何自信。自信并不等于自負,也不等于高傲。隻要在正确認識自己的情況下,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然後盡量朝着能夠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對自己撒謊。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楊绛先生在《一百歲感言》中說:“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系。”
也許我們不漂亮,也許我們不富有,甚至可能也談不上品德高尚、勤勞勇敢,但我們仍有表達的權利,我們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裡任性而有光彩地活着。
我拍的照片普普通通,我可以發朋友圈嗎?我的腿有點粗,我能穿裙子嗎?我的學曆不高,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嗎?……
答案是:絕對可以。
不要小心翼翼,不要如履薄冰,你是自己生活的國王/女王,隻要你不把手伸到别人的生活當中,你就可以暢快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參考文獻
[1]車麗萍. 健康人格與自信[M]. 人民出版社, 2011.
[2]車麗萍, 黃希庭. 青年大學生自信的理論建構研究[J]. Xinlikexue, 2006, 29(3): 563–569.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6.03.011.
[3]梁燕,崔麗瑩.自戀對初中生合作行為的影響:自尊穩定性的調節作用[J].心理研究,2019,12(02):187-192.
[4]于權. 健康的自戀使人充滿信心[J]. 青年科學, 2008, 2008(1): 30–31.
[5]GILL R, ORGAD S. The Confidence Cult(ure)[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015, 30(86): 324–344. DOI:10.1080/08164649.2016.1148001.
[6]LEE S Y. How Do People Compare Themselves with Other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Case of Facebook[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 32: 253–260. DOI:10.1016/j.chb.2013.12.009.
[7]MILLER J D, LYNAM D R, HYATT C S. Controversies in Narcissism[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7, 13(1): 291–315. DOI:10.1146/annurev-clinpsy-032816-045244.
[8]MORF C C, RHODEWALT F.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1, 12(4): 177–196. DOI:10.1207/S15327965PLI1204_1.
[9]O'REILLY, C A, DOERR B, CALDWELL D F. Narcissistic CEO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4, 25(2): 218–231. DOI:10.1016/j.leaqua.2013.08.002.
[10]SHIPMAN A S, MUMFORD M D. When Confidence Is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Overconfidence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1, 22(4): 649–665. DOI:10.1016/j.leaqua.2011.05.006.
(學生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