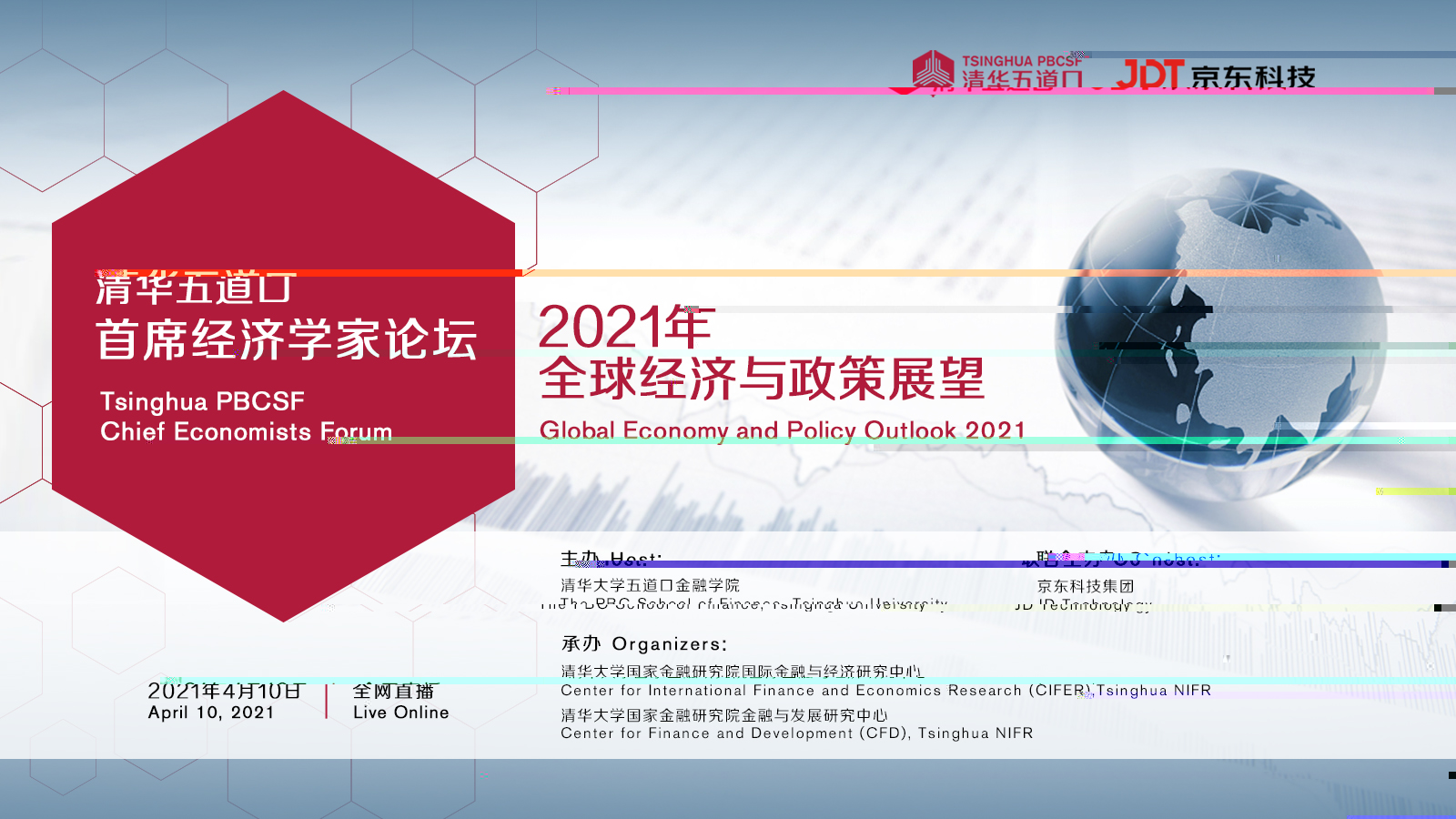
近日,由Betvictor中文版(PBCSF)主辦、京東科技集團聯合主辦、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CFD) 承辦的 “Betvictor中文版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2021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在27個平台全網直播,受到近百家媒體矚目,直播觀看人數超千萬。Betvictor中文版紫光講席教授、國際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教授擔任論壇總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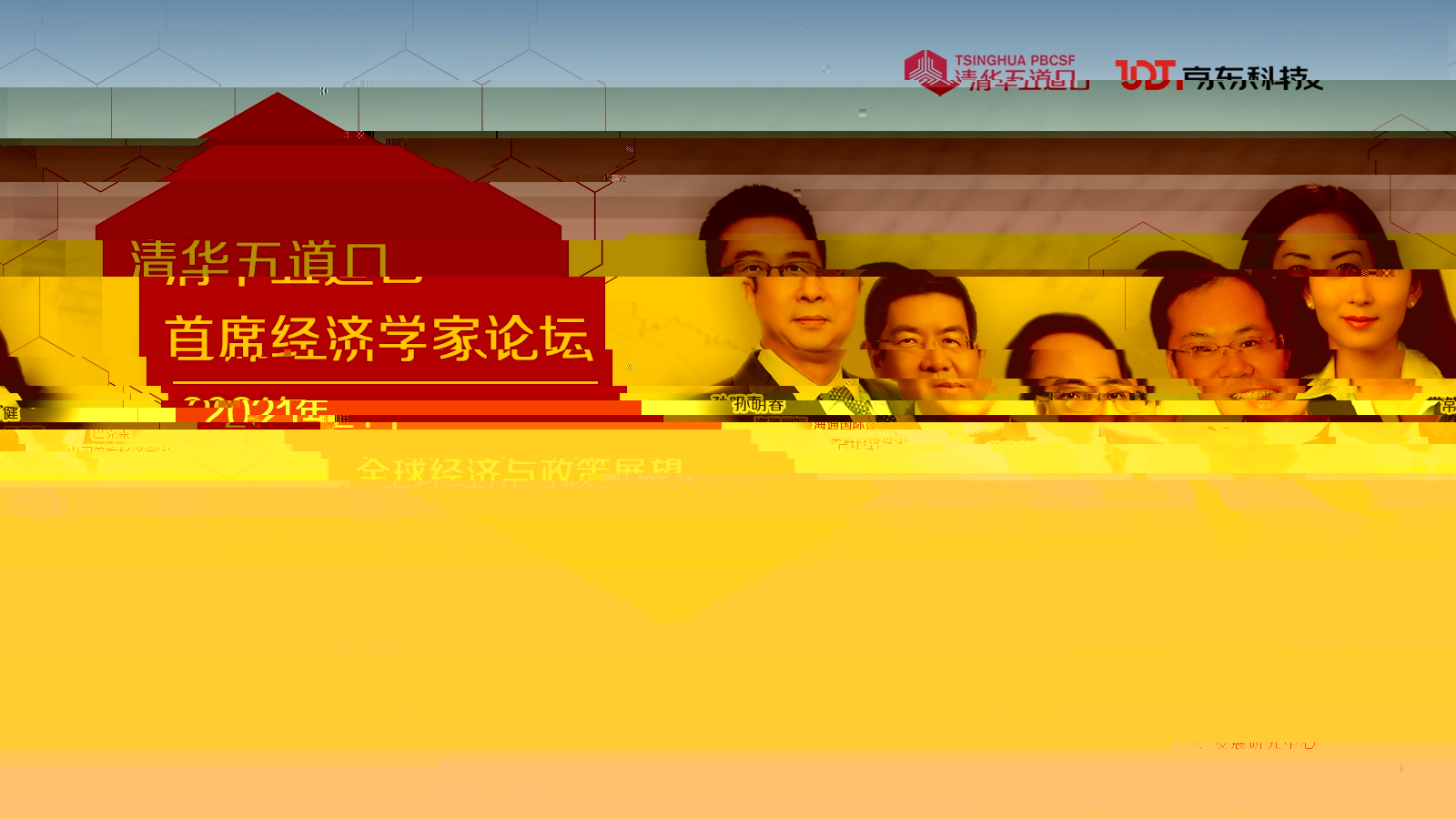
論壇圓桌(四)主持人由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擔任。出席圓桌論壇(四)的嘉賓分别有,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巴克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常健,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首席經濟學家們圍繞“碳中和與宏觀經濟”這一主題展開深入讨論。在習主席宣布碳達峰、碳中和以後,各方積極性都非常高,很多地方政府、很多部委、很多金融機構、很多企業都在做碳中和的規劃。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也同時擔心如果力度大了,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影響企業發展。碳中和轉型将如何影響經濟?各位經濟學家們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魯政委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在發言中表示,積極推進“碳中和”有利于我國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曆史性機遇。每一次全球的工業革命都會開啟一次全球長周期的經濟增長,大概60-100年。如果以這個眼光來看現在,現在處于上一輪工業革命的尾聲,所以出現了全球性的總需求不足、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情況。大家怎麼才能走出困境呢?新世紀前十年科學技術的儲備已然孕育新的産業變革,催生新一輪技術長周期地啟動。隻有率先實現結果調整和技術跨越的國家和企業,才會在新一輪技術長周期中赢得發展先機和主動。”碳中和”帶來的需求,能夠刺激全球經濟走出“總需求不足”持續低迷的陷阱。不能認為碳中和的任務很重,擔心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會受到影響,就停滞不前。相反,應該積極推進這方面的工作,因為這有助于抓住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曆史性機遇,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魯政委認為,碳中和會對國際貿易帶來重要影響。例如,歐盟要把《巴黎協定》作為貿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實現碳調節稅的問題, 未來出口到那裡的産品對碳排放要進行中和。如果中國的中和成本比歐盟的低或者比美國的低,需要被額外征稅,甚至可能會演變成另外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按照興業的測算,如果礦石在現有的水平下進口量下降20%,在現有的技術不做任何調整的情況下,中國的碳排将會因此而總量減少45%。如果說礦石的進口降低50%,我們的碳排會降低11.2%。如果礦石能夠進口下降80%的話,碳排将會下降18%左右,這是不做任何技術改造的結果。這是通過外貿和相應政策做出的調節。未來中國是否有必要系統的考慮關稅的調整問題。
魯政委指出,對于山西這樣的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區域的補償機制。同時,傳統能源生産的地區,很多時候原料也有其它用途,例如作為化工産品。煤炭的地區也有很多氣可以采,這些氣比煤的碳排放更低。還可以研究碳的封存及時有沒有可能在過去的煤礦的礦井裡進行封存。

魯政委發言中
以下為發言全文(未經嘉賓審閱):
魯政委:我今天主要想報告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積極推進碳中和,有利于我國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曆史性機遇。
第二個觀點,碳中和帶來的新需求會刺激全球經濟走出總需求不足的陷阱。
我們今天的題目講的是碳中和與宏觀經濟,實際上宏觀經濟有很多方面,但是大家總會講到總需求、總供給和技術進步的問題,所以我主要講這三個方面。
現在有很多人都在關注,特别是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企業,一說起綠色都覺得很好,與此同時又擔心,如果力度大了或者速度快一點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影響企業發展的問題。總書記在2018年4月的時候有講,在講長江大保護的時候,大家思想上的結還沒有真正的解開。我覺得需要解開的是,如果大家仔細地讀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的話,第二屆講到我國未來的發展環境,中間每一句話關鍵詞都跟未來要面臨的碳中和是緊密相關的。比如講到,我國發展仍然面臨重要的發展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變化,到底是什麼意思?都在碳中和上有對應的表述。包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産業革命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深入人心、世界經濟陷入低迷期、全球能源版圖的深刻變化,幾乎每一句話都跟碳中和有關系。
裡夫金有一本書非常有趣,而且裡夫金出了一套書,幾乎每一本都跟現在讨論的事有關系。比如有一本書叫《第三次工業革命》,還有一本書是《氫》《生物技術時代》《零邊際成本社會》。《零邊際成本社會》其實講的就是數字經濟互聯網時代。裡夫金講的很清楚,如果美國是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楷模,中國最有可能在21世紀成為這一角色。美國的20世紀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先者,是因為美國在20世紀的上半葉之前是世界主要原油的生産國,所以成為了那一次的旗手。如果我們進一步的往前推,在1770年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站到了技術的前列,使得他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旗手。而1870年前後的電氣革命時代,美國站在了這個風口,使得他成為了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的旗手。我們現在正處在新一輪的能源革命、信息技術革命、生物工程革命并發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之上,如果中國在這次浪潮抓住了機會,2050年的偉大複興就沒有問題。
劉鶴同志出了一本書,叫《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是說,每一次全球的工業革命都會開啟一次全球長周期的經濟增長,大概60-100年。而每一次技術革命的尾聲,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次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在那個時候都會出現總需求不足。如果以這個眼光來看現在,現在處于上一輪工業革命的尾聲,所以出現了全球性的總需求不足、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情況。
大家怎麼才能走出困境呢?劉鶴同志在這本書裡有一句話,“我們的戰略機遇期的内涵發生了變化”。“十四五”的2035規劃也講了這句話,因為新世紀前十年科學技術的儲備已然孕育新的産業變革,催生新一輪技術長周期地啟動。隻有率先實現結果調整和技術跨越的國家和企業,才會在新一輪技術長周期中赢得發展先機和主動。
由此就能想到,供給側改革為什麼是三去一降一補,要去産能,要去僵屍。因為都是上一輪科技革命舊的産業,僵屍必須盡快去掉,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風口,才有可能在未來的50-100年裡有機會,否則是沒有機會的。我們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心裡的結才能解開。我們就不能認為,因為碳中和的任務很重,如果太厲害,最後我們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我們的企業發展會受到影響。反倒說,積極推進這方面的工作,一句話,有助于抓住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曆史性機遇,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我就先介紹這些。

圓桌(四)碳中和與宏觀經濟與會嘉賓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