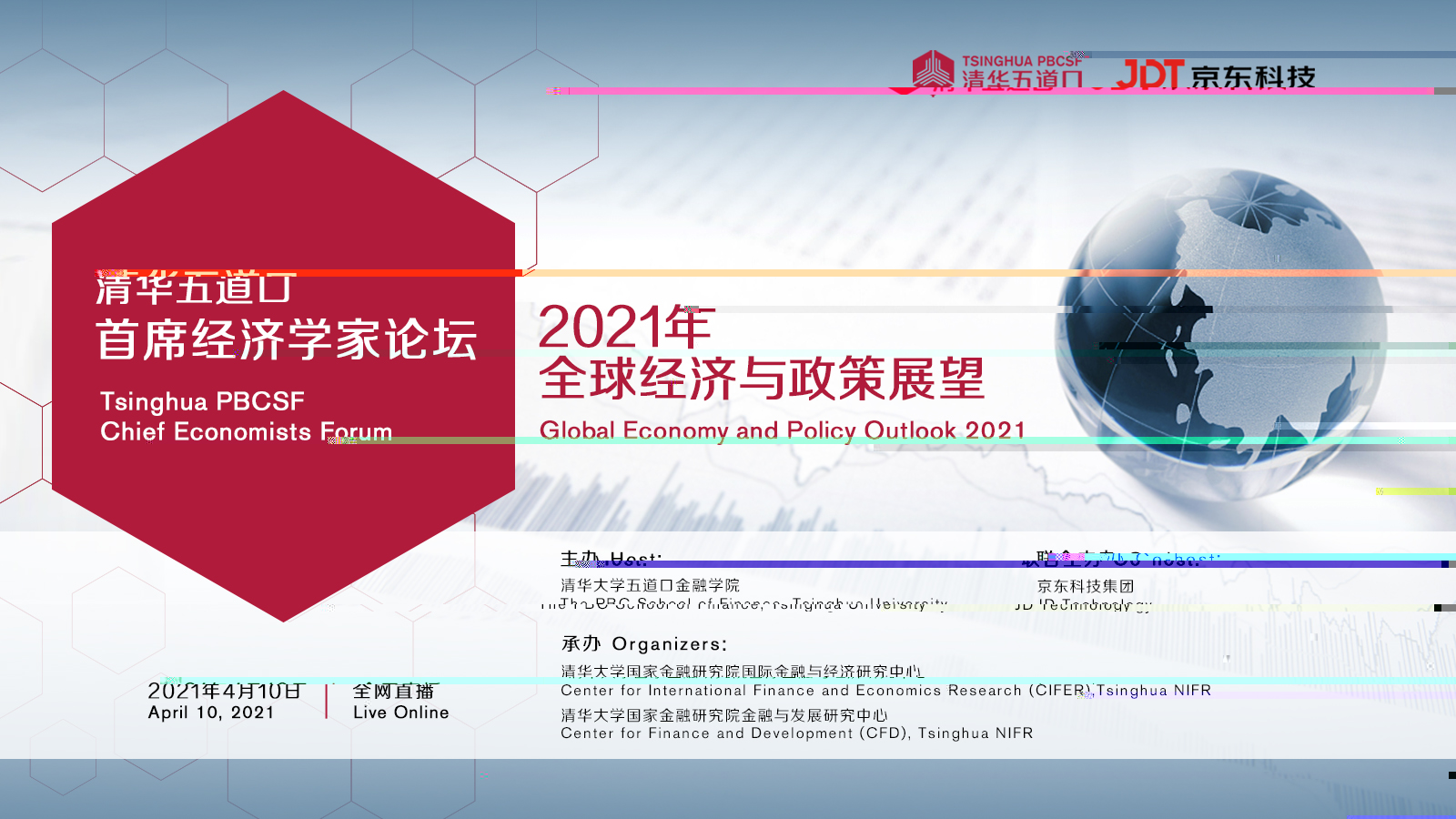
近日,由Betvictor中文版(PBCSF)主辦、京東科技集團聯合主辦、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CFD) 承辦的“Betvictor中文版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2021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在27個平台全網直播,受到近百家媒體矚目,直播觀看人數超千萬。Betvictor中文版紫光講席教授、國際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教授擔任論壇總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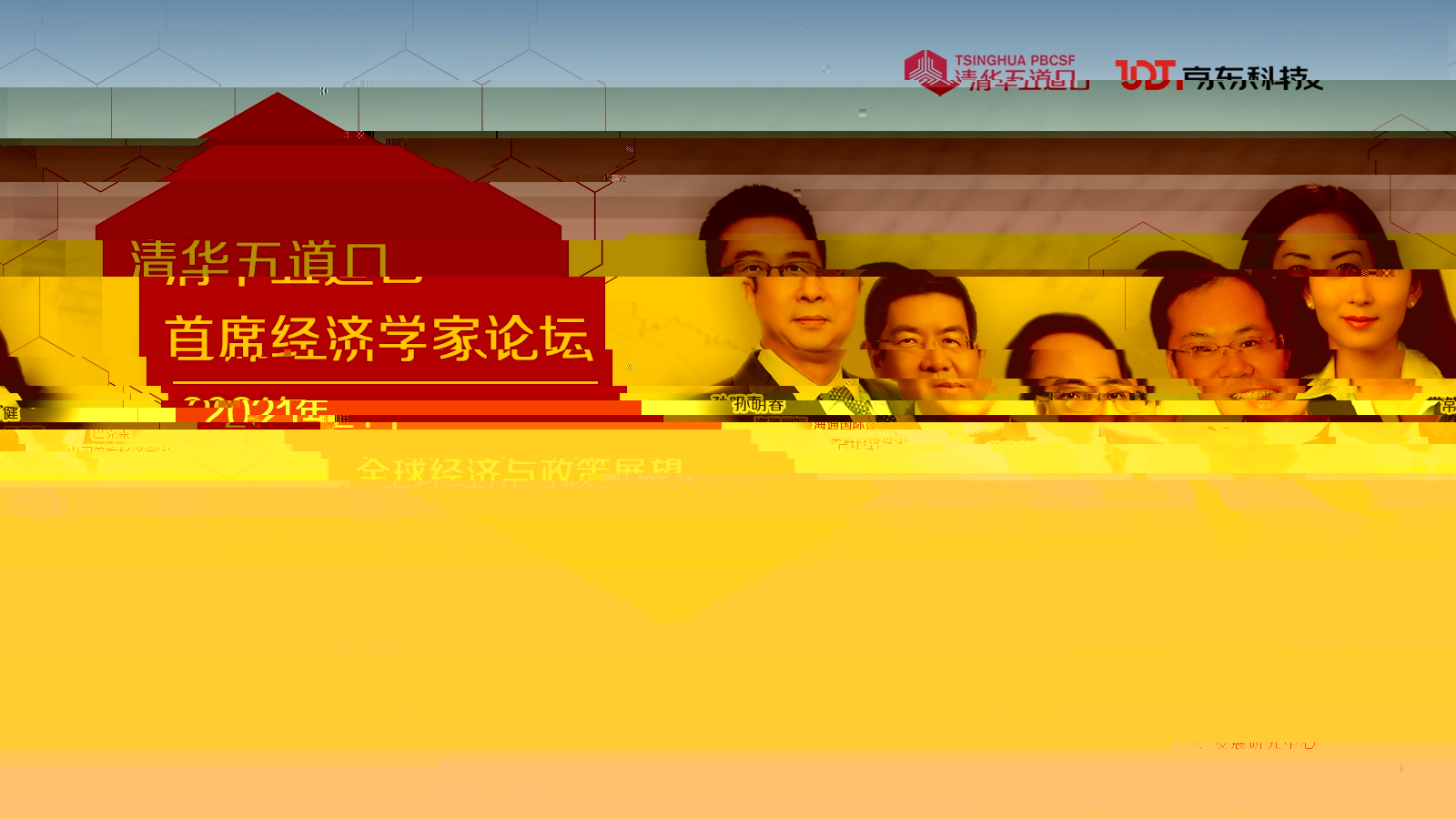
論壇圓桌(四)主持人由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擔任。出席圓桌論壇(四)的嘉賓分别有,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巴克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常健,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首席經濟學家們圍繞“碳中和與宏觀經濟”這一主題展開深入讨論。在習主席宣布碳達峰、碳中和以後,各方積極性都非常高,很多地方政府、很多部委、很多金融機構、很多企業都在做碳中和的規劃。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也同時擔心如果力度大了,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影響企業發展。碳中和轉型将如何影響經濟?各位經濟學家們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馬駿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在發言中表示,至少要從四個維度來看碳中和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一是額外的投資。中國未來三十年走向碳中和可能需要額外的幾百萬億的投資,對需求有很大拉動。二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也降低通脹風險。過去十年在光伏、風電設備的技術進步已經使其成本下降了80%,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如果其他新能源如氫能、海上風能有了重大技術突破,整體的能源成本可能會大幅度持續下降。三是政策因素。碳中和不會自動發生,必須要有配套出台很多政策,包括能源政策、環境監管政策、綠色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碳市場政策等。這些政策會影響整個經濟體的不同行業和消費者的行為。四是一個國家的進出口潛力和進出口環境會影響這個國家是受益還是受害。如果一個國家大量進口石油,例如中國,碳中和以後就不需要進口了,全部用本地生産的可再生能源,因此是個利好。另外一個角度,一個國家有沒有出口很多跟碳中和相關的技術和産品。中國有這個能力,因為中國既是制造業大國,也有很大的市場,規模效益很大,成本可以降得很低。光伏風電設備、電池技術都可能成為全球非常有競争力的技術,出口到全球更大的市場。
馬駿指出,在面對碳中和的機遇,各地反應差異很大。有些沿海地區非常積極,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能夠提升他們的經濟增長潛力。 因為會帶來更多的投資,尤其是綠色低碳的投資,帶來技術進步和引進人才,甚至能開拓全球市場。但是也有地方在考慮怎麼充分利用碳達峰的十年期繼續規劃傳統的能源和高碳的項目。但若十年之内提高了峰值,以後碳中和就會非常困難。對于整個經濟碳強度太高的區域,例如山西,直接與煤炭相關的經濟領域達到60%,這也是一個真實的挑戰,涉及當地的資源禀賦問題,除了引進産業和人才,也需要外部的援助幫助他們改變戰略和觀念。
馬駿介紹,碳中和對宏觀經濟和經濟結構會産生巨大的影響,尤其在投資機遇和金融風險兩個領域當中,投資機遇在今後三十年将達到100萬億到300萬億人民币。同時,金融機構若繼續停留在高碳的産業和企業中,也會面臨違約率升高和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的風險。
馬駿認為, 綠色低碳的投資可能會給金融機構帶來很多的融資、承銷、服務的機會。同樣,退出高碳産業也會帶來機遇,比如最近已經開始有轉型債、轉型基金等等,這些金融服務是幫助高碳企業盡快的轉到低碳和脫碳,這個過程中也需要金融服務。
關于碳中和對經濟影響的研究框架,馬駿作了三點總結。第一,需要在宏觀經濟層面有一個比較有質量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碳中和所帶來的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這個框架應該是動态的、跨周期的模型,将氣候模型和能源模型融入宏觀經濟模型。 第二,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帶來的投資機遇和對投資所帶來的挑戰。挑戰主要是高碳行業對金融穩定的影響,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不隻是金融機構,央行作為金融穩定的主管機構也應該進行分析。 第三,碳中和會帶來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區之間的不均衡分配、行業之間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導緻某些經濟體、某些産業的大幅度萎縮甚至造成失業。如何保證一個比較公平的轉型,讓社會穩定不要受到太大沖擊,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題目。

以下為發言全文(未經嘉賓審閱):
馬駿: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特别高興代表Betvictor中文版主持這場關于碳中和與宏觀經濟的讨論,我們也特别高興有四位重量級的首席經濟學家參加這次的圓桌讨論。這個議題大家都很清楚,起源就是習主席在去年9月份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要在2030年之前做到碳達峰,2060年之前要實現碳中和。宣布了以後,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非常之高。過去幾個月,我已經看到了很多地方政府、很多部委、很多金融機構、很多企業都在做碳中和的規劃,大家普遍認為,從應對氣候變化角度來講,這是一個裡程碑的事件,因為中國是排碳量最大的,占全球的30%。有了中國的承諾,我們就可以保證本世紀内絕大部分國家都能夠達到碳中和。如果中國沒有這個承諾的話,本世紀不一定幹得了這個事。
同時,對宏觀經濟、對經濟結構也會産生巨大的影響,有些是倒逼性的影響,金融口已經有了很多的讨論,尤其是在投資機遇和金融風險兩個領域當中。基本的共識是,投資機遇恐怕是在100萬億到300萬億人民币之間,這恐怕是今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風險也很大,如果還繼續待在高碳的産業和高碳的企業當中,銀行貸款的違約率可能會很高,作為投資機構資産回報率可能會大幅度下降。最近我參與讨論了很多共識,但是對宏觀經濟還沒有深入的讨論,今天請到了四位宏觀經濟學家,讨論碳中和對宏觀經濟有什麼影響,對GDP、通貨膨脹等等,當然也要考慮對産業的影響,産業對地區的影響同時也會帶來收入分配的效益,今天是主要的話題,但是也不排除,嘉賓可能會讨論綠色金融方面的議題。
馬駿:謝謝海洲。我非常同意,尤其是兩個方面,我再呼應一下。一個是碳中和有利于增強制造業的升級轉型的動力,通過規模效應可以降低成本。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迹象。比如說過去十來年光伏、風電設備,由于規模的效益,所以成本降的非常之快。過去十來年,技術進步導緻了光伏和風電的發電成本下降了80%多,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除此之外,制造業的強項也有巨大的出口潛力。不光是中國的市場、全球的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的市場,都是可以享受規模效益的空間。
另外一個是關于通脹方面,我特别同意海洲剛才講到,如果搞的好的話,能源的單位成本會下降。什麼意思?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意思,光伏、風電成本已經降低了80%,未來十年可能還會降低50%。如果其他新的能源有重大突破,比如氫能、海上風能,整體的能源成本可能會大幅度持續下降,所以未必會帶來整體性的通脹。我就呼應這麼兩句。
馬駿:謝謝魯首席。其實,我最近在地方上也參加了很多讨論,不同的地方就像你講的,他們對于碳中和的反應不一樣。有些沿海地區已經在考慮要實現2050年的碳中和,比全國的目标還要提前十年,他們非常積極,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能夠提升他們的經濟增長潛力。為什麼?因為會帶來更多的投資,尤其是綠色低碳的投資,帶來技術進步,引進很多人才。說不定他們把綠色科技的項目做好了以後,還能獲得全球的市場,這是沿海一些地方非常積極正面的反應。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反應非常不一樣,有些地方在考慮怎麼充分利用碳達峰的十年期繼續上一個高碳的項目。覺得還有十年,反正還沒有達峰,還在規劃傳統的能源項目和高碳的項目。這個做法挺危險的,因為十年之内把峰值搞的很高的話,以後碳中和就會非常困難。還有一些地方主要是因為整個經濟碳強度太高。舉一個例子,就是山西,現在整個經濟體當中大概60%都是跟煤炭相關的,有些是直接跟煤炭、煤電相關的,有些是跟煤炭相關的設備制造、運輸等等。如果煤炭以後不能做了,那怎麼辦?經濟當中百分之五六十就沒有去處了,這個問題倒是一個真實的挑戰,可能涉及到本地的資源禀賦的問題,有沒有機會引進綠色低碳的産業、引進人才,當然也有對碳中和理解的問題。這些問題一時半會不一定解決得了,還需要外部的援助幫助他們改變戰略和觀念。
馬駿:謝謝常健。我想也借此機會做一個簡單的綜述,也講講我的觀點。
為什麼我會提這麼一個問題?宏觀經濟分析怎麼把碳中和納入進去,部分的原因是兩三年以前,有8個國家的央行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一起發起了一個央行綠色金融網絡(NGFS)。我前兩年在這個網絡當中擔任監管工作組的主席,現在我又擔任研究組的主席。一直在讨論這個問題,到底傳統的央行系的宏觀經濟模型怎麼反映氣候變化和碳中和産生的效果。實際上都沒有說清楚,目前是83個國家的央行、監管機構都在網絡裡面,也都在比較掙紮的研究這個事,所以今天提出來和大家一起讨論和頭腦風暴一下。剛才講的觀點我多同意,我想至少有兩點是共識:
第一,這些分析框架一定是動态的,氣候變化和應對氣候變化都是中長期的事,不可能在原來預測一個月、三個月的模型當中有所體現。
第二,不可能僅僅在傳統的CGE模型或者是DSGE模型裡面有效的反映出來,必須要納入其他元素,比如說氣候變化的模型、能源結構轉型的模型,要跟經濟模型融合起來才能獲得投入的信息。具體考慮什麼因素呢?有幾大因素要考慮:
一是額外的投資。中國未來三十年要走向碳中和的話,可能要有額外的幾百萬億的投資,一定會對經濟從需求角度來講有很大的拉動,這是可以反映進去的。
二是技術因素。傳統經濟學模型,技術是個固定的東西,生産函數是固定的,這是不對的。生産函數随着碳中和相關的低碳零碳技術的變化不斷地在變化,系數在變化,需要能源等等其他的技術因素要放進來。
三是政策因素。因為碳中和不會自動發生,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政策,能源的政策、環境監管的政策、綠色金融的政策、财政的政策、碳市場的政策,等這些政策全部放進來以後,會影響整個經濟體的不同行業和消費者的行為,可以在模型框架裡得到很好的反映。這些國家的進出口潛力和進出口的環境會影響這個國家到底是受益還是受害。如果這個國家是大量進口石油的,就像咱們國家,未來碳中和不進口了,全部用本地生産的可再生能源,像光伏、風能、氫能,那是一個利好。從進出口的角度來講,咱們就可以把更多的進出口留在中國。
另外一個角度,這個國家有沒有能力出口很多跟碳中和相關的技術和産品。我們是有這個能力的,因為中國的市場這麼大,我們的規模效益很大,成本肯定會降的很低。像光伏風電的設備、電池的技術都可能成為全球非常有競争力的技術,讓我們能夠出口到全球更大的市場。
這些因素全部放進去,才會有比較完整的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分析框架。

圓桌(四)碳中和與宏觀經濟與會嘉賓合照